之前,大象公会在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母系社会进行分析,认为母系社会阶段并不存在,而母系社会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它是一种神话。母系制是“异常的”甚至是“落后的”,而“父系关系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来,我们好好说说大象公会这篇文章。先说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一,这篇文章采用了“人类学”的知识,但它本身的认识论是反人类学的。
作者认为母系社会数量稀少所以可以忽视其存在,这其实是有违人类学的精神内核。人类学正是通过发现、进入、以及深入的描述【主流以外】的族群和文化来挑战所谓“主流”的观念、反思自身文化的合理性、并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遭遇提出质疑。
一个人类学家或者人类学爱好者面对任何“少数派”的文化或行为立即应该想到的是:
他们和我们为什么不同?
他们的选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的选择真的是最好的吗?
他们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自身文化中怎样的盲点?
是不是还有其他生而为人的方法?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be human】
通过对一个【弱小的他者】的反复追问与刻画,扩展了我们对人类这个生物群体的认知,增加了对人类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敏感度,以至于最终才能对“异常”产生理解和包容。
而大象公会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人类学认识论的反面。
作者因为“他者”的稀少和弱小便抹杀它的存在(作者说是反对阶段论,但同时又把“母系社会”定性为“神话”,这点后面再说)。而另一行为模式因为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便合理化其存在,丝毫没有任何反思和质疑,这在我看来是远比不知道人类学知识更严重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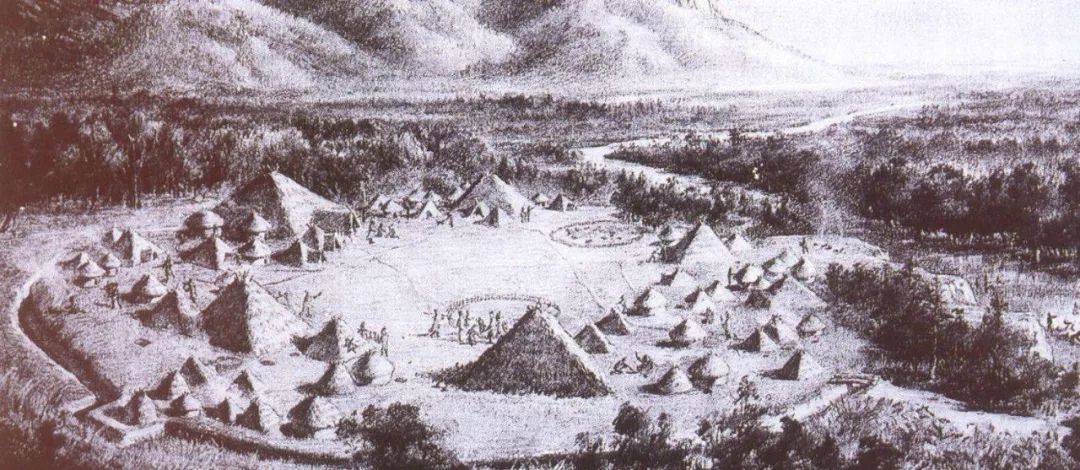
第二,通过黑猩猩的行为来合理化人类类似或相同的行为模式和组织模式。
这就更扯了。虽说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历来相处不是很融洽,但也没哪个生物人类学家敢跳出来跟ta的文化人类学同事说,“看,黑猩猩这样做,所以人类这样做是合理的”。
这是根本误解了生物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对灵长动物的研究不是为了给当代人类背书,相反,是因为灵长动物可以完成某种类似于人类的组织和行为,借此来了解人类的过去,也就是说人类的进化历程,认识人是如何从动物中突颖而出,一步步脱离动物成为人。
是用人类的行为模式去考察动物的进化阶段,而不是以动物的行为来解释人类的文化逻辑。这篇文章恰恰是反其道而行。如果黑猩猩在某种环境下发展出一些行为模式,那么人类做同样的事是不是就都具有合理性了呢?显然不是。否则人类大概是赤身露体茹毛饮血也无可厚非才对。

归入正题。人类历史上有没有母系社会阶段?没有。但人类到底有没有母系社会?当然有!
作者以母系社会阶段论为批判对象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摩根提出的人类社会文明阶段论被打入冷宫有100年了吧?在其之上的马恩的发明也不大在教科书中看见了吧?现在中学教科书中还有吗?如果有,那作者这个科普至少还有一个可取之处。
但接下来作者把“神话”的标签一股脑的贴在“母系社会”而非“母系社会阶段论”上的做法就不妥了。对女性人类学家关于母系社会的理论更显得无知。用黑猩猩的研究直接背书人类父系体制真的就是……胆子很大了。
首先,作者是怎么推断出母系制度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以至于可以用「神话」来消解的?
母系制度在2019年的今天是少数派没错,甚至有人称摩梭族是最后的母系社会,虽然这么说有误导之嫌,但也足以证明母系制在现代文明中的稀少和落魄。
但这并不能反推出母系制的产生是一件“异常的”甚至“落后的”的事情(作者在对摩根阶段论做出批评的同时自己却常常陷入其陷阱)。
因为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假定了产生父系制的条件——“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才是唯一产生亲属关系的“正常条件”,而母系制的产生条件——热爱和平与协作——就是“特殊”或者“非正常”的产生条件。
这显然是因果倒置了。

任何社会形态和人类行为模式在其独特的地理分布、生态环境、物资分配、以及谋生手段等众多因素下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说是“特殊”的,是人类在ta当下的处境中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秉性做出的arbitrary——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决定。
这决定可能是以父亲来组织亲属关系,或者以母亲来组织亲属关系,但无论哪一种,都是最适合那一群人在那个环境下的存活的。
这种选择本身没有好坏,只有“有效”还是“无效”。
既然父系和母系共同存活于世千百年,那么在其各自的文化土壤中,显然这两种亲属关系模式都是“有效的”,都有其产生的根源、必然性、和优越性,都是适应这个人群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好的选择。
要知道,母系社会的衰败并非来自于自身的“衰落”或者“无效了”,而是在与父系文化碰撞中,输了。
这是结果。但这结果不能反推母系文明的产生比父系文明落后,这只能证明父系社会更擅长征服与战争而已。在好战且善战的父系文化面前,母系文化的消亡几乎是注定的。

其次,母系社会并非只是个神话。虽然母系阶段论是为迷思。
如果你在JSTOR搜“母系社会”,出来的未筛选的结果是14299条文章条目。如果单选人类学,也有5279条文章条目。面对这么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们对母系社会的研究,断言母系社会只是个神话,真的是一个严谨和负责任的态度吗?
纵观所有这些文献和民族志,可以列举出来的母系社会肯定是这一篇回答容不下的。仅列举一些比较有名的吧:
太平洋岛国上的Chuuk人和Pulap人,
因为马林诺夫斯基而闻名于世的Trobriand人,
印度尼西亚的Minangkabau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母系社会,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边界处的Toka人,Luapula人,
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的Guajiro人,
北美印第安人部落Hopi和Navaho,
新几内亚的Nagovisi人,
加纳境内的Ashanti人,
苏丹的Uduk人,
当然还有我国云南境内的摩梭人
这列出来的只是所有研究里的10分之一不到吧。事实上,很多太平洋岛国、大洋洲的岛国、印第安人的部落、以及非洲的部族都是母系社会。其分布之广、人数之众,和父系制度可以说是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亲属关系格局。今天母系社会的衰落和消亡,刚才说了,并非其自身有什么不好,母系社会更和平,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和谐,凶杀和暴力行为更少见,要说有什么不好,自然是“太软弱”——在与崇尚暴力和征服的父系社会碰撞过程中,必然落败。
最后,作者对女性人类学者对母系制度的研究也是充满误解。
作者的认知是,女权主义者亲睐母系阶段论的理由很简单:假如漫长的前文明时代都是母系社会,那么母系制乃至母权制就可以说是更自然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
女权主义者可能有时激进,但不傻。
我就想问这么愚蠢的观点真的是女权主义者的吗?还是一些人自己对学者的文章断章取义、囫囵吞枣的误读?
—— “前文明都是母系,母系就更自然?“ 前文明人类还住洞穴呢,还拿着棍子追野猪呢,那么穴居和拿棍子狩猎也是更自然、更符合人类本性的?这么傻的结论是谁想出来的?
再说,社会科学对母系社会阶段假说早已抛弃,作者自己也承认这点了,那么大多是社科背景的女权主义者怎么可能会用母系社会阶段论来为女性权益背书?其他学科的女权主义者我不了解,但至少女性人类学家对母系社会对理解和解读远比作者呈现出来的聪明多了。

我拿Maria-Barbara Watson-Franke发表在Anthropos上的一篇论文《Masculinity and the “Matrilineal Puzzle》[1]举个例。
Watson-Frank讨论了一个困扰很多学者的问题——“Matrilineal Puzzle“。
这个puzzle说的是,一个男性在母系社会中的身份与职能的撕扯。因为母系社会的权力关系核心是兄-妹、母舅-外甥的关系,而非夫妻关系,那么一个男人如何协调他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与作为兄弟和母舅的关系呢?最初学者认为这两重关系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当他要履行丈夫和父亲的职责时,往往要面临来自母系一方兄弟和母舅的压力。
Watson-Frank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puzzle之所以成为puzzle,恰恰是因为我们带入了父系制度下的父权视角,因此无法想象一个男人怎么可能放弃其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特权。正因为无法放弃,所以才有撕扯。
而很多母系社会呈现出来的现实,却是男人们丝毫没有感到什么撕扯,因为他们并没有西方父权社会中,父亲和丈夫必须要成为权威的那种对权力的迷恋和执着。相反,母系社会中男性气概的塑造也和父系社会中男孩子建立男性气概的方式皆然不同。
在西方,如同一切的父系社会,“性”是整个权力关系的核心。
男性通过“性”建立对女性和子女的特权和掌控,女性通过和男性结婚获得他的姓氏成为明媒正娶,子女通过在正式的婚姻关系中诞生获得父亲的姓氏成为子嗣、财产和名号的继承者。所有的经济行为、社会关系和权力格局都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展开的。
也因此,男性对权力、金钱和地位的控制必然表现在对妻子和子女的控制上。而一个男孩子要成为一个男人,也必须获得与之相称的“男性气概” —— 要独立、冷漠、彪悍、好斗、要去占有、去征服,藐视女性、疏远子女,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等等等等。
但这一切在母系社会中都呈现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母系社会中,性和权力被分割开来了。
你看,和女性发生性关系赋予你丈夫的头衔,但权力的掌握却是在女性的兄弟手中;男性的精子产生他们的子嗣,但子女的继承确是从母亲和母舅这一线下来。性不再产生权力,权力也不再依赖于对性关系的占有。
这意味着什么呢?
—— 意味着“世上一切都关于性只有性关乎权力”这句话就失效了啊!在母系社会,性并不关乎权力,性也只是日常事物中好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平常常的事。
因此,母系社会中的父亲和子女的关系也远非父系社会中那样紧张。子女不直接从父亲那里继承,子女在父亲的眼中就是单纯的最可爱的宝宝,由于对子女的规训主要由母亲和母舅实行,父亲基本上就只要宠着子女就行了。这种描述和我自己在摩梭社会的见闻是完全一致的。父亲和子女的关系真是比我们社会中的亲子关系轻松愉快太多。
而在母系社会中男子气概的塑造也和父系社会完全不同。后者要求男孩子独自、坚强、冷漠、好斗。但母系社会的男性在成长经历中,女性,往往是母亲是子女的榜样和力量和智慧源泉,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以勤劳、顾家、担当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为荣,不会因为是男孩子就不做家务,也不会因为是女孩子就可以不读书。而女性作为经济生活的提供者,也令男孩子从小就知道敬重女性的力量和能力。一个男孩子不会对自己具有某些女性特征而感到忧虑和紧张,也不会负担要变得更强、更tough、更具有攻击性等特质。就像大量人类学民族志和文献中记载的那样,很多母系社会中发生强奸、性侵、家庭暴力的情形几乎为0。
女性以及女性研究的人类学者眼中的母系社会,绝不是大象公会的作者所刻画的那样,把母系社会很傻很天真的视为「史前天堂」。母系社会是父系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性不总是和权力连接在一起,不是所有的丈夫和父亲都要压制和掌控妻子和子女,男孩子也不总是在一个备受责备和压力的环境中长大,男性气概并不是总代表坚强、冷漠、好斗和粗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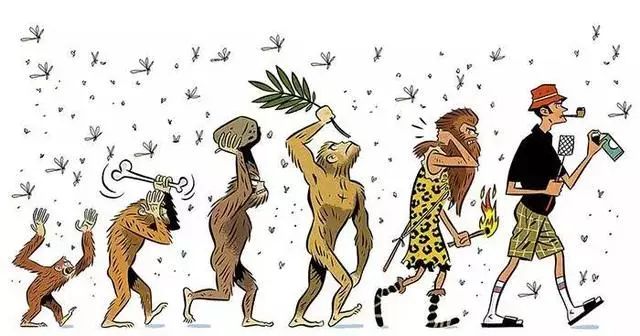
最后,再来看作者对父系社会很有代表性的一段描述:
“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组织控制能力等等制度性因素,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作者认为“父系关系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且不说这里用“进化”的概念是多么“摩根主义”,我们姑且用“发展”来替代“进化”。
如果说人类学对母系社会的研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那这启发一定是:父系社会所推动的这个人类发展的方向真的是对的吗?真的是好的吗?真的不需要反思吗?真的不会面临瓦解和消亡吗?我们真的不会从越来越稀少的母系社会中学到点什么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想这些问题。
